一个湖北村庄的防疫故事-村医穿雨衣当防护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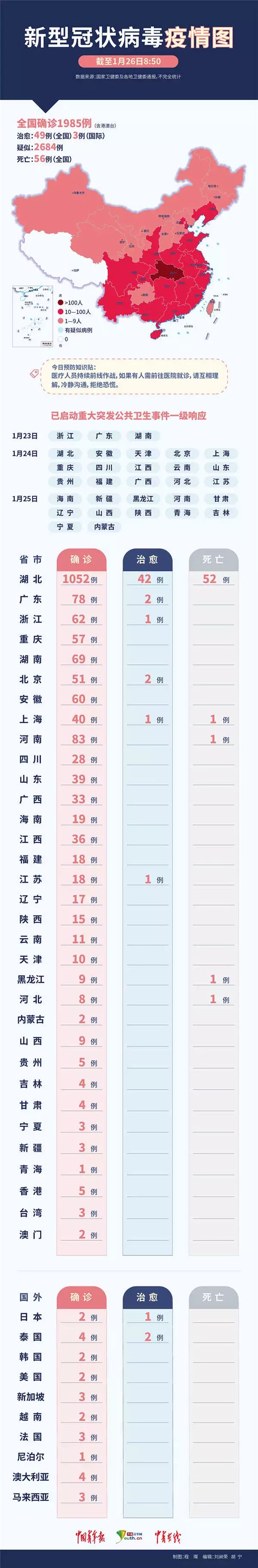
作者 秦珍子编辑 张国农历庚子年初一早上8点多,湖北村医张茹芳(应受访人要求化名)出门上班。她的防护装备是:一件雨衣、一双雨靴、一副平光眼镜。她在雨靴外又套了一双鞋套。晚辈笑她,“非主流混搭”。 丈夫建议她工作时戴上摩托车头盔,她试着戴了一下,感觉重,放弃了。这是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的一个村子,距离武汉市200多公里。张茹芳所在的村医务室一共有两名医生,日常服务的村民则有两三千人。她在这里平静工作了几十年,直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她成为农村医疗体系应对疫情的末端环节。从早上7点开始,村里的公共喇叭就不断以“命令式口吻”播音:禁止串门,禁止聚餐。村委会的灯又亮了一夜,24小时有人值班。几天以来,到医务室看病的村民较往常减少,但来的人症状都比较类似,主要是发烧、咳嗽以及其他“看起来像感冒”的情况——考虑到防疫形势,没有此类症状的村民尽量避免去医务室。大部分时间,张茹芳都在给看病的村民们普及新型肺炎病毒知识,“一种来源不明的病毒,初期症状和感冒差不多,但也可能不发烧”。有发热情况的,她赶紧让患者去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就诊,可以初步判断为普通感冒的,就给一些药品让在家观察,“防止在医院交叉感染”。据她观察,村民的防护意识近几日明显提高。春节前“返乡潮”到来时,随着年轻人归来,麻将馆也火爆起来,需要抢位置或提前预定。如今,很少有人再去打麻将了,串门拜年的人也少了很多。来医务室的村民几乎都戴了口罩,甚至还有戴“N95”的。镇上的药店口罩“限购”,每天“可凭身份证登记购买”。腊月二十九夜里,村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,按照镇里传达的要求,发放“预防肺炎”的传单。每天,镇干部会挨村“巡逻”,去村委会、各村医务室查看,甚至会在路口劝退过年走亲访友的人。村干部会排查“返乡人员”和有红白喜事计划的家庭。有的村子每天“监控返乡村民体温”,将记录上报。所有村庄按照镇上的应急通知,“红事一律取消,白事尽量从简”。荆州市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,“酒店、宾馆无条件接受宴席、房间的退订退费”。张茹芳所在的医务室平均每天接触患者及家属超过100人。全镇有10多个农村医务室,包括她在内,村医们向镇里提出需要防护服。“我一旦被感染,会感染很多人”,她解释。最终,他们每人分到一套从县里协调来的防护服。防护服“很薄”,套在冬衣外容易破,且不能反复使用,“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”不舍得穿。张茹芳如今就用雨衣雨靴代替防护服。谨慎起见,她上班时同时戴3个口罩,每隔几小时需要更换口罩时,她会取下紧贴面部的那一个,再在最外面戴上一个新的。靠着镇上分配的10个口罩,加医务室原来的一点储备,她和同事撑了3天,终于等到新供给。大年初二早上,她接到了镇上的通知,医疗物资已经到位,可以去镇卫生院领取。此前,医疗物资紧缺是一个明显问题。张茹芳在外地工作的侄女对记者表示,除夕夜她的同乡们一直在通过社交网络呼吁,转发荆州市中心医院、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、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的“接受捐赠”公告。张的女儿曾向荆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朋友求助,希望给母亲找来一套防护装备,却被告知“我连口罩都要去外面买,哪来的防护服”。有人在群里发了“用文件袋制作护目镜”的视频,张茹芳的丈夫看到了,去给妻子找来了雨衣和摩托车头盔。对于“新型肺炎”,村民们的态度时而重视,时而轻视。美国“撤侨”的消息传来,引起一轮紧张;每天通报的“治愈患者”数量增加,紧张就又会缓解。武汉要建“小汤山”,大家的反应是:“医院装不下了吗?”一打听,四里八乡没有“确诊”的人,又觉得没事了。张茹芳年轻时被派到城市“学医”,村老支书对她说:“我们要培养一个’永久牌’,不是’飞鸽牌’,一定要回到村里。”新型肺炎疫情出现后,家人劝她别去上班了,她犹豫过,还是去了,“都是乡亲,太熟悉了,不可能不去”。她坦言,一个人在家时也觉得很害怕,哭过好几次:“敌人是谁?敌人在哪?都不知道啊。手里也没有武器,搞不好还会连累全家人。”但当穿上白大褂,她又觉得压力小一些,“这是我的职责”。每天下班回到家,张茹芳会用84消毒液擦洗雨衣,用酒精擦拭钥匙、锁、门把手和她触摸过的家具。为了保护家人,她坚持在家里也戴着两层口罩,和家人分房而睡。全家人吃饭时用公筷分菜,并且尽量用一次性餐具。她会端着饭菜到远离丈夫和女儿的地方吃。镇里进入了紧张的防疫状态。镇政府连轴转,没人过年休假。县城也是如此,初一晚上,有人在凌晨接到了镇领导发布的通知,告知各村要调用辖区内货车封闭路口,派专人把守,除应急救援车辆一律限行;各村连夜安排,“落实封闭自保行为,不谈条件,不谈报酬,战时状态,十万火急”。此前,江陵县的防控指挥部已经连续发布1、2、3号通告,宣布实施包括公共交通线路停运、外地返乡人员健康登记、营业场所关闭、交通要道设置疫情检测点等措施。初一早上,张茹芳出门前,门口就有村民来访,希望进屋看病,她没同意。但病人进家这种情况难以避免:她晚上一回家,又有老人为咳嗽的妻子而来,找她开药,打量她一番问道:“还戴着口罩?你怎么这么怕死!”她早就想好了,接下来还要去镇上采购些一次性雨衣,“明天脑袋上一定要套个塑料袋”。(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,首发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头条号,加入树木计划。)
Edit
Publish
Last updated